| 新闻 | 视频 | 博客 | 论坛 | 分类广告 | 购物 | 简体/繁体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关于万维 | 登录/注册 |
 |
|
莉莲是那天早上唯一的病人。在芬顿医生开始收取年费之前的日子里,她习惯了拥挤的候诊室,这是一种改变。“礼宾医疗”听起来像“定制的巧克力”,不可能是莉莲的天性,但她还是留在了诊所。寻找一位新医生需要打电话,会见陌生人,填写病史表格,即使对一个 51岁的健康人士来说,这也可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莉莲也许可以忽略两次流产——感谢上帝,不是所有的经历都会留下痕迹——但她是否也可以忽略两次分娩,第二次是剖腹产?医生们在办公室里闲聊,有时是关于孩子的。
一笔费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用撒谎或解释。莉莲并不介意说出真相,但真相可能令人吃惊,让人感到不安,莉莲称这种状态为“惊慌失措”。
蒂娜年龄在 50 到 60 岁之间,不是个健谈的人。她似乎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看着莉莲,这让她想起了伊丽莎白·鲍恩在她的一部小说中描述一个特工的方式——“同时用两只眼睛”。这种联想或许不太公平。为什么蒂娜不应该用两只眼睛严厉地盯着莉莲的脸呢?护士既不是独眼巨人,也不是患有外斜视。
莉莲的右臂没有供血。蒂娜叹了口气。“不,”她说。“没什么。”
“嗯,我今天早上喝了很多水,”莉莲说,这句话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才是唯一重要的。
“还不够,”蒂娜说,然后转向莉莲的左臂,这证明是成功的。
她双臂上的静脉曾经是 coöperative。莉莲正想说些什么——比如一只胳膊在某天早上醒来,决定不守规矩是多么奇怪——但蒂娜举起了一根手指。“听着。如果你保持安静,你就能听到。”
它吗?
“血流,”蒂娜说,对着手里的管子点头。
莉莲屏住了呼吸,在寂静中,她在心里详细地记下了护士的样子和动作。她的指甲被涂成了淡紫色;她的头发,齐肩长,浓密,被染成了墨黑色;她那绿色的眼影和粉色的腮红似乎只是为了突出她棱角分明的脸和严厉的目光。她喜欢用左手,用它给管子上盖和解盖。她的右手手背上长了一颗痣。莉莲没有对艾琳做过这样的盘点,她的脸已经开始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但艾琳从来没有让她听她自己的血液填充试管。没有护士做过这样的事。
莉莲想,也许蒂娜有一种倾向,想从她的工作中寻求不寻常的、美学上的满足,尝试着慷慨,但这是一种冷酷的慷慨,她的感觉使她确信自己拥有变色龙的轻松:她可以用热情和热情洋溢来应付艾琳的闲聊,她也可以用她自己的冷漠来匹配蒂娜不笑的静止。她想知道蒂娜是否要求她所有的病人都听他们的血液。似乎不太可能。不管有没有礼宾服务,都会有人抱怨的。他们坐着度过了六根大管子和三根小管子的沉默。只有一次,莉莲听到了她以为可能是自己血流的声音。如果让她描述一下,她肯定没有办法说出来。莉莲是个作家,但文字有限。有一次,在动物园里,她和孩子们应邀去抚摸一条大蟒蛇。莉莲害怕爬行动物,但为了孩子们,她还是鼓起勇气,用手指摸了摸蟒蛇的背部。这种感觉不像触摸任何其他生物或无生命的物体,无法形容。有些体验是排他性的,只有那些寻求或被它们折磨的人才知道。
蒂娜解开莉莲手臂上的止血带,拿着一盘管子离开了。在那一刻,莉莲有两个想法:如果蒂娜是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她可以很好地描述她们;而蒂娜,她的外表和举止令人难忘,永远不会是小说中的凶手,只是一个诱饵。
在现实生活中,护士伪装成杀人犯的可能性虽然不是零,但也很低,莉莲不相信自己会发生这种耸人听闻的转变。她只是最近看了太多的悬疑小说,那些书往往会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注入额外的意义。它就像一幅画中的天空,这往往是莉莲在博物馆里首先注意到和研究的东西。那一定是画家们想要的,他们个人的天空被他们的感知和技巧渲染得独一无二。莉莲对实际的天空没有同样的关注,她仔细观察的其他事物都是以天空为背景的:二月的金缕梅,五月的垂樱,秋天的树叶,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里的冰柱。她不愿像托尔斯泰习惯的那样,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广阔而崇高的天空赋予任何隐喻性或先验性的分量。
七年前,在她的大儿子奥斯卡(Oscar)去世三个月后,莉莲开始去看芬顿博士。芬顿博士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很专业地处理了这些信息。她问莉莲心情如何,莉莲用一个关于她的垂直与水平比例的笑话来回答。开玩笑是她无法控制的泪水,但芬顿博士既没有笑,也没有追问莉莲傻笑背后的原因。相反,她写下了莉莲的精神科医生和治疗师的联系方式,并将注意力转向莉莲的身体,莉莲认为,这提供了混凝土的安慰:小问题可以处理;任何重大问题都会转介给专科医生。
但是,当第二次死亡困扰着莉莲的生活时,芬顿博士的反应让她大吃一惊。那是裘德死后四周,莉莲因为园艺上的小事故去了诊所。一根玫瑰刺扎进了她的无名指背,引起了极度疼痛的局部感染。
芬顿博士解释说,在两个关节之间的地方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就像一个小的培养皿。“就像埃彭多夫试管,”莉莲说。对于作家来说,总是想要修改和编辑,这是一种职业危害;她忍不住提出了另一种明喻。芬顿博士看了一眼莉莲,说:“是的,没错。在那个空间内,细菌的增殖可能会引起急性疼痛,但这个问题很容易用抗生素解决。”芬顿博士在水池边洗手,准备结束这次探视时,她询问了莉莲的总体健康状况。莉莲犹豫了一下,说还有一件事芬顿博士可能想知道,这与感染无关,也不是预约的原因。
这一次,莉莲没有开玩笑。她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消息:和他哥哥一样,裘德自杀了。芬顿博士看起来很伤心,莉莲担心芬顿博士会晕倒,就抓住她的胳膊肘,把她领到椅子上。这是莉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目睹另一个人对裘德的死的反应。除了两个亲密的朋友外,其他人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得知这个消息的——不是莉莲发的,也不是亲自来的。芬顿博士的眼泪使莉莲觉得她耍了一个不公平的把戏。她应该在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手指扎破赶到诊所之前,把消息用电子邮件发过去。
莉莲之所以选择芬顿博士,是因为她看待生活的方式既简单又务实。“我的工作”——她经常在莉莲的检查中说——“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你的健康。然后,当时机成熟时,希望你能尽快出院,没有长期的疾病,痛苦最小化。”芬顿博士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她用笔在空中画了一条稳定的线,然后突然把它放下了。莉莲笑了,但芬顿博士仍然很严肃,只是对莉莲的理解点头。
当芬顿博士从眼泪中恢复过来时,她问莉莲过得怎么样。莉莲意识到自己的双手现在正被芬顿博士握着,在那一刻,他既不严肃,也不讲求事实。她回答了一个经过精心构思的问题,作为人们提问的答案,做出了一个只有一些人会注意到的区别:“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再好起来了,但我过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他……你知道吗?”
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向莉莲脱口而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尽管这肯定是任何人最先想到的问题之一。“我觉得‘为什么’不是我该问的问题,”她说。“我接受裘德的决定。”
“你一定是个圣人!”
这是一句令人费解的感叹,莉莲后来对此感到纳闷。什么样的圣人,属于什么样的宗教或传统?莉莲不是圣人,只是考虑到这个想法,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比现在暗淡十倍。她也不是一个冷血的怪物,尽管她知道有些人正是这样认为她的。不然为什么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会选择自杀呢?深不可测是令人不安的,这让最平庸的思想成了避难所。那些不认为自己是怪物的人,如果灾难可以被解释为后果,他们就不会那么不安。“我想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自然的,”莉莲和她的治疗师沉思了几次,有一次是在伦敦的一个文学宴会上,和一个熟人。
莉莲上一次见到伊梅尔达是在伦敦,当时伊梅尔达就坐在她旁边,那是十年前,当时她的孩子们还活着,但对有些人来说,闲聊是一种侮辱。伊梅尔达沉思着。“如果你环顾四周,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和你一样的困难,”她指着正在享受晚餐和交谈的穿着考究的客人说。“所以,恐怕一般人会想,天哪,那些父母一定是怪物。”
莉莲觉得这个回答很安慰。别人为自己选择的有色眼镜,不可能使她的世界变得更暗或更红润。她宁愿和一个能够看清世界本来面目的人交谈,因此也能看清她是谁。“有时候我会想到艾薇·康普顿-伯内特,”莉莲说,她知道伊梅尔达会理解她的意思。艾薇最小的两个妹妹在 1917 年圣诞节的一次自杀协议中死去,她们甚至不是那个家庭中唯一遭遇英年早逝命运的孩子。
伊梅尔达说:“一百年前,年轻人的死亡是一种更常见的经历。
“但这种想法对你没有帮助。” “不,”莉莲同意了。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发生的事情而自责。”
“哦,我不自责,”莉莲说。“生活已经这样做了。”
蒂娜回来做了更多的检查。虽然不是一个健谈的女人,但她有一系列的方式来传达她的判断:沉重的叹息,急促的喘息,或者强烈的摇头。因此,莉莲得知她在双眼深度知觉测试中并没有取得好成绩,而且她的握力也不是最理想的,这是一项重要的测试,因为它与痴呆症的发病有关,因为蒂娜刷新了莉莲的记忆,尽管她不需要这样的提醒。
正当莉莲坐到椅子上准备做听力测试时,蒂娜停了下来,指着挂在衣架上的莉莲的羽绒服。 “看,”蒂娜说。背面有一处裂口,大约有半英寸。一些毛茸茸的绒毛就要漏出来了。 “哦,”莉莲说,她的脸和声音都很平淡。她感到一阵抽搐,不是因为这件夹克衫,而是因为她十二岁时穿过的那件。那一年,她开始了去中学的通勤,在北京拥挤的公交车上穿行,清晨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大都市的公共交通,是加速童年结束的可靠方式。在这些公共汽车上,一个女孩学会了小心男人的身体部位,一只手有意地探查,一条腿卑鄙地压迫,但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这个世界的恶意对莉莲来说是明确的。一个陌生人在她羽绒服的后背上刮来刮去,纵横交错的纹路让她感觉不到。她下车后,身后的羽毛开始乱飞,被风吹起,被附近的路灯照得泛着金橙色。一个过路人叫了一声,莉莲周围围了一圈人:比被灾难包围更糟糕的是让陌生人来评价它。不止一个人对莉莲的粗心大意表示不满;有人大声质疑她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一件羽绒服,在 1985 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个碰巧路过的熟人对不必要的野心的代价提出了质疑。这位女士说,莉莲本来可以去附近的中学上学,而不是走很远的路去学校上学。从几十年后的角度来看,那一刻充满了童话般的奇幻气息,但那是一个关于蓝胡子的故事,而不是关于鹅女孩的故事,是一个警世故事,而不是一个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多年以后,莉莲理解了人们对不可理解的事情的恐惧:当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某人身上时,肯定是这个人一开始就犯了错误。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人们还能怎么找到安全感和安慰呢?
蒂娜似乎被莉莲的冷淡冒犯了,她咂了咂舌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创可贴。“如果你允许的话,”她说,在莉莲同意之前,她把创可贴贴在撕裂处。
当蒂娜抚平创可贴时,莉莲看着她的薰衣草指甲,想起了一个典型的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场景——也许这只是莉莲的想象,因为后来她想不起她从汤姆·里普里的哪本书中保留了这种记忆:汤姆把他刚谋杀的人的尸体搬到树林里,不小心折断了一棵小树的树枝;尸体在燃烧,汤姆抚摸着受伤的树,充满了温柔的道歉。
羽绒服没有感觉到它的残害。树不会哀悼被砍断的树枝。流入试管的血液不渴求观众。一根玫瑰刺没有任何恶意,只有盲目的固执。莉莲想,如果把生活中的人和事加起来,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感情的:不能感情或者不愿感情,不过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在很多方面,一个没有感情的世界也许没有一个感情过于狭隘、过于强烈、过于胆怯或过于扭曲的世界支配生活那么可怕。
过去的一对双胞胎经常出现在莉莲的记忆中。一年级时,莉莲和女孩们成了朋友。他们家不像莉莲的大多数同学,他们住的不是有中央供暖和自来水的公寓楼,而是一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窗户是开着的正方形,上面贴着一层层的报纸,房间里主要是一张砖床,大得足以让父母和四个孩子合住。这对双胞胎,连莉莲当时都无法理解,他们养了一只刺猬作为宠物,而且只有一次,莉莲被邀请在放学后去看望这只刺猬。姐妹俩的哥哥都外出了,父母也都在上班。房间里既没有足够的自然光,也没有一盏灯,这让莉莲想起了“中世纪”这个词,她刚学过这个词,尽管她知道不能和朋友们分享。事实上,这对双胞胎在学校里被认为是落后的。他们不识字,周一的卫生检查也经常不及格:他们的指甲是黑的,脖子后面和耳朵后面的皮肤看起来是乌黑的,他们从来不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
这只刺猬是从它住的纸板箱里捡出来的。(为什么它从来没有想过在没人在家的时候爬出盒子逃跑?莉莲在拜访之后会想。)这个生物长着一双小眼睛,一个粉红色的、会抽泣的鼻子,长着灰色的、不伤人但只会挠痒的尖刺,没有名字。不像猫,它不能追逐一根纱线,但它可以做最巧妙的把戏,这对双胞胎急于向莉莲展示。其中一人在莉莲的掌心放了一撮盐。刺猬舔了舔,然后开始咳嗽,一种怪异的人声,好像是一个老人在咳嗽。莉莲吓了一跳,扭头看了看门口,姐妹们笑了:莉莲也被骗了,就像那只刺猬一样。
莉莲觉得有必要和姑娘们一起笑。当过于强烈的感情比表达出来更容易被掩盖的时候,这是孩子们闲聊的一种形式吗?难道这就是莉莲不流泪而讲笑话的习惯的开始吗?
几周后,两个女孩和她们的母亲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父亲和两个男孩幸免于难。没有人提起刺猬,莉莲早已忘记了姑娘们的面孔和她们的名字,她想起了刺猬。莉莲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因为想起那只咳嗽的刺猬使她痛苦,然而她也没有感情,因为她没有哀悼她的朋友。也许困扰一个人的是徒劳,而不是痛苦、羞辱和死亡。除了从女孩们手中偷走刺猬之外,莉莲无法阻止她们从无助中获得无情的快乐,就像这个世界无法拯救女孩们或其他许多孩子一样。也许莉莲应该告诉伊梅尔达,孩子的死亡并不是变得不那么常见了。相反,这个世界在让人分心的事情上变得越来越机智:无用比死亡更容易被驱逐。听力测试开始后,蒂娜第一次表示赞同。“我的上帝,你的听力很好,”她说,直视着莉莲的眼睛,好像在挑战她不同意。莉莲想,她可能是太过关注了,才想象出了这些东西,就像托尔斯泰赋予奥斯特里茨高远的天空以意义,或者像过去的画家赋予他们所看到的天空以不朽的意义一样。
莉莲发出不确定的声音。她并不介意艾琳的闲聊,因为这既不需要她的感情,也不需要她的注意。蒂娜要求莉莉安付出额外的努力——她故意让自己看起来很迟钝。假装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解,或者是不理解。
大约十五年前,莉莲去纽约北部旅行。那是她过去常说的纳博科夫乡村,不过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她意识到叫它“magaccountry”更合适。之前邀请她去的那个文学组织安排了从机场到小镇的汽车服务,两个小时的车程。来接莉莲的那个人介绍自己是诺亚。
这不是莉莲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被俘虏了。了解她的人往往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听众,把她的安静看作是关注,把她的问题——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她的问题——看作是一种邀请。有一次,在旧金山的一个筹款派对上,一位女士带着渴望的神情走近莉莲。“如果我母亲有你这样的事业,她就不会自杀了。”这是开篇的一句话,莉莲觉得有必要留下一段很长的叙述,并给出适当的回应。还有一次,别人的研究生导师让莉莲在她的办公室里独白了三刻钟,在这段时间里,莉莲一句话也没说。之后,那个年轻人惊呼道:“你太棒了。也许我应该在我的小说中加入一个聪明的日本女人作为角色!”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一位理发师——他是纽约的移民,在家乡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一边给莉莲理发,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论宗教、哲学,以及他与信仰的斗争。
莉莲常常想,人们总有一种想和陌生人谈论自己的冲动,不管他们生活的时间长或短,这真是令人惊讶。但很少有人会在审视自己的生活时,认为自己的经历微不足道;他们一定觉得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生活,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坚持告诉莉莲他们的故事?只有像艾薇·康普顿-伯内特这样的人才会说,在她抚养的那些年幼的兄弟姐妹去世后, “我的生活如此平淡无奇,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
人们有时是自以为是的,有时是可预测的,但往往两者兼而有之。然而,即使在莉莲向朋友哀叹的时候,她也知道自己对一再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负有部分责任。她是不是太被动了,太客气了,太同情了,太善良了——这是不是让人们觉得向她介绍自己很轻松呢?她是不是太好奇了,以至于无法抗拒一个故事——任何故事,好故事、坏故事或平庸故事?还是她最终对自己被别人的愿望和误解所挟持的困境过于漠不关心?
在纳博科夫国家的旅程,本可以成为那些熟悉的事件之一。在她的旅行中,莉莲无意中收集了许多司机的故事:一个来自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家庭的男人为了逃避他所谓的“天主教内疚”而向西跑,一路跑到太平洋;一个波多黎各人想成为冠军骑师的愿望因青春期体重增加而破灭;一个宾夕法尼亚的祖父,他讲的关于每一个孙子的才能和怪癖的故事——他们七个——让莉莲昏昏欲睡;还有许多陌生人的厄运和好梦。莉莲想知道这些人是否会把他们的故事重复给所有的乘客听。
诺亚受到莉莲偶尔礼貌的回应的鼓舞,不出所料地讲了个不停:关于他以前的职位,学区负责人;谈到两年前父亲从豪华轿车公司退休后,他继承了一个车队;他的曾曾祖父从中欧的一个村庄移民而来,他的家庭每隔一年聚会一次,轮流在旧大陆的村庄和纽约州北部的小镇之间举行,最近一次聚会有 250 名来自两国的家庭成员;他的三个孩子,最小的在上高中,两个大的在上大学;关于他最喜欢的杂货店 Wegmans,以及他最喜欢从店里买的有机烤鸡。人们不知疲倦地需要讲述他们的生活,莉莲想,一半听,一半沉浸在有趣的绝望中。
然后,诺亚改变了话题。他问莉莲是否听说过一个著名的案例:当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被一个男人绑架,并被锁在一个农舍的地下室里 7 年。“我想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原因是,我们很快就会通过这一部分,”诺亚说。“我可以绕道带你去看房子。”
莉莲说没有必要,诺亚坚持说这并不不方便。只有两分钟的路程,他会确保踩油门,这样莉莲就可以毫不拖延地到达她的酒店。车里的空气似乎已经有了一种不同的品质。莉莲面无表情,假装没有看到诺亚的眼睛在后视镜里打量着她,而他则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这个女孩被绑架的经历,她在地牢里的岁月,以及最终她的逃脱。
诺亚并不是那个犯下暴行的人,但他比那个罪犯强多了,他一定很佩服那个罪犯的壮举,因为他从当地的高速公路上拐进了一条乡村公路,然后又拐进了一条没有铺砌的土路。据诺亚说,这所农舍已经好几年没人住了,在早春的时候显得单调乏味,白色的油漆已经剥落,黑色的窗户茫然地凝视着。诺亚让汽车空转着,指着屋后一条通往邻近农场的小路。诺亚说,当那个女孩找到逃跑的机会时,她光着脚在那条小路上奔跑,描述当时的情景,就好像那天他坐在同一地点的一辆空转的汽车里看着一样。
也许诺亚和帕特丽夏·海史密斯没有什么不同,帕特丽夏·海史密斯没有杀人,但看到她笔下的人物杀人时一定会感到兴奋。诺亚把自己变成一个强迫性的叙述者,因为他安全、自由、不可战胜,而且因为莉莲除了坐在他身边倾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抚弄着可怕的细节,这是一种犯罪吗?
从那时到后来,莉莲都在想,当汽车停在农舍前时,她保持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是否做得对。他们回到高速公路后,她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诺亚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胆小,在另一种意义上无耻——是显而易见的,但让他知道她看透了他是没有意义的。她的理解正是他所渴望的:他希望她的想象被他的想象所框定;他想要她一心一意的关注和强烈的感情。当他们到达旅馆时,诺亚帮莉莲卸下行李箱,并祝她旅途愉快。在此之前,莉莲并不知道这次旅行将如何结束。在小说里,在农舍和旅馆之间会有很多选择。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会把故事往一个方向发展;伊丽莎白·鲍文,另一位;艾薇·康普顿-伯内特,又是一位。但莉莲知道,除了等着瞧,她别无他法。在小说中,人们可以操纵时间线来强调戏剧或化解危机,但在生活中,莉莲当时和后来都知道,这种操纵是虚假的:当一个孩子死亡或第二个孩子死亡时,母亲无能为力;她只能等待每一天的到来,然后去发现那一天的意义。
有些作家靠的是技巧;有的,靠他们的癖好。尽管如此,每个作家的笔触都有一致性,海史密斯就是海史密斯,鲍文就是鲍文。生活,前后不一致,技巧不多却有不可预测的特质,永远是一个优秀的说书人。
当蒂娜回到房间时,莉莲躺在检查台上,光着身子,只穿着内裤和一件长袍,双手紧握着,因为蒂娜警告过她不要系腰带。蒂娜给心电图机接上了电线,给莉莲的脚踝戴上了手铐,做了一次 ABI 测试,问了两次莉莲那天早上是否擦了乳液。
莉莲闭上了眼睛。在悬疑谋杀案中,蒂娜可能给莉莲注射了什么东西,或者她可能只是用钝器把莉莲击昏,但生活不是虚构的。无论那天早上蒂娜的不满背后发生了什么,无论诺亚想象中发生了什么,都只是浩瀚现实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不太可能改写一段平凡的人生。很少有人能做到。很少有人愿意。
测试结束后,蒂娜将电极从莉莲的身体上断开,小心翼翼地不要太突然地撕下胶带。当蒂娜说她的心脏看起来很好时,莉莲仍然闭着眼睛点了点头。然后房间变得安静了,好像蒂娜离开了,莉莲没有注意到。她睁开了眼睛。蒂娜正站在桌子旁边,低头看着莉莲的脸。“你有孩子吗?”蒂娜问。
后来,莉莲会打电话给一位父亲是医生的朋友,确认这个问题不寻常,或者至少不专业。后来,莉莲会想,在芬顿博士的档案中,是否有蒂娜看到的关于奥斯卡和裘德死亡的笔记,以及蒂娜是否觉得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莉莲选择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意义。当然,这是一种猜测;这一次,莉莲不想知道真相了。
但在那一刻,莉莲从检查台上抬起头来看着蒂娜,她的黑发衬托着她不苟言笑的脸,她既没有犹豫,也没有退缩。“不,”她说。
蒂娜点了点头。“我也不知道。”
这句话中明显的悲伤让莉莲大吃一惊。蒂娜的意思是,莉莲和蒂娜一样,错过了女人生命中重要的东西,这太糟糕了吗?或许蒂娜期待莉莲说:“我有两个儿子,但他们都死了”——蒂娜本可以用自己的启示来回答:“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我也失去了我的孩子。”
莉莲永远不会知道蒂娜悲伤的背后是什么。在她离开后,芬顿博士走进了检查室,莉莲没有向医生提起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就像几年前,她没有向文学组织抱怨诺亚一样。诺亚和蒂娜会留在她的记忆里,就像那对双胞胎姐妹一样,但他们不会对莉莲造成什么困扰,不像刺猬的咳嗽,不像她背上飞舞的羽毛,也不像她孩子们的生死。如果奥斯卡和裘德还活着,莉莲对蒂娜的感觉可能会有所不同。她可能会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出一些故事。她甚至可能编造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名叫诺亚的恶棍。但她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几天她的感情也更加排他性。她并不想去理解蒂娜和诺亚,因为理解不是他们应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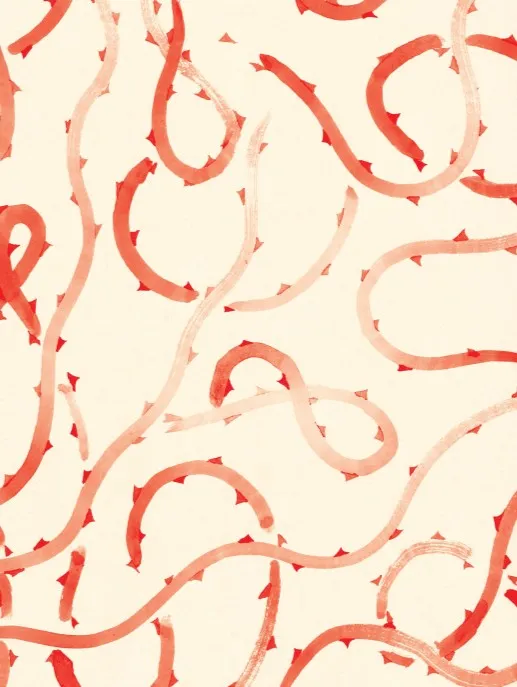
李翊云自 2003 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她的作品包括入围 2024 年普利策奖决赛的故事集《Wednesday’s Child》,以及回忆录《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
| 当前新闻共有0条评论 | 分享到: |
|
||||||||||
| 评论前需要先 登录 或者 注册 哦 |
||||||||||||
| 24小时新闻排行榜 | 更多>> |
| 1 | 王毅如“过街老鼠” 党媒装疯卖傻 |
| 2 | 张又侠“枪指挥党” 政治局势力版图大变 |
| 3 | 他才是中南海变天关键一子 |
| 4 | 趁习不在 公安部人事突变 |
| 5 | 中国人“生死轮回”的说法 很可能被证实是 |
| 48小时新闻排行榜 | 更多>> |
| 一周博客排行 | 更多>> |
| 一周博文回复排行榜 | 更多>> |